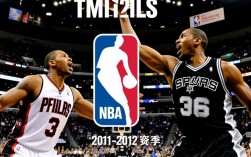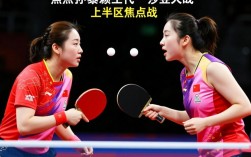《当加害国学者拿起放大镜:日本学者著作如何还原日军毒气战全貌》
从“否认”到“自查”:日本学术界的转向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日本历史教科书对“毒气战”几乎只字不提,右翼言论更把“化学武器”归为“战场谣言”,转折发生在1984年——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在防卫省战史室偶然发现《攻占武汉战役中的化学战实施报告》,首次以日方档案证实: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,华中派遣军曾大规模投射糜烂性毒弹,此后,粟屋宪太郎、松野诚也、奈须重雄等学者陆续加入,形成一支“自查毒气战”的学术梯队,把被刻意掩埋的加害历史拉回公共视野。
三大“拼图”让真相浮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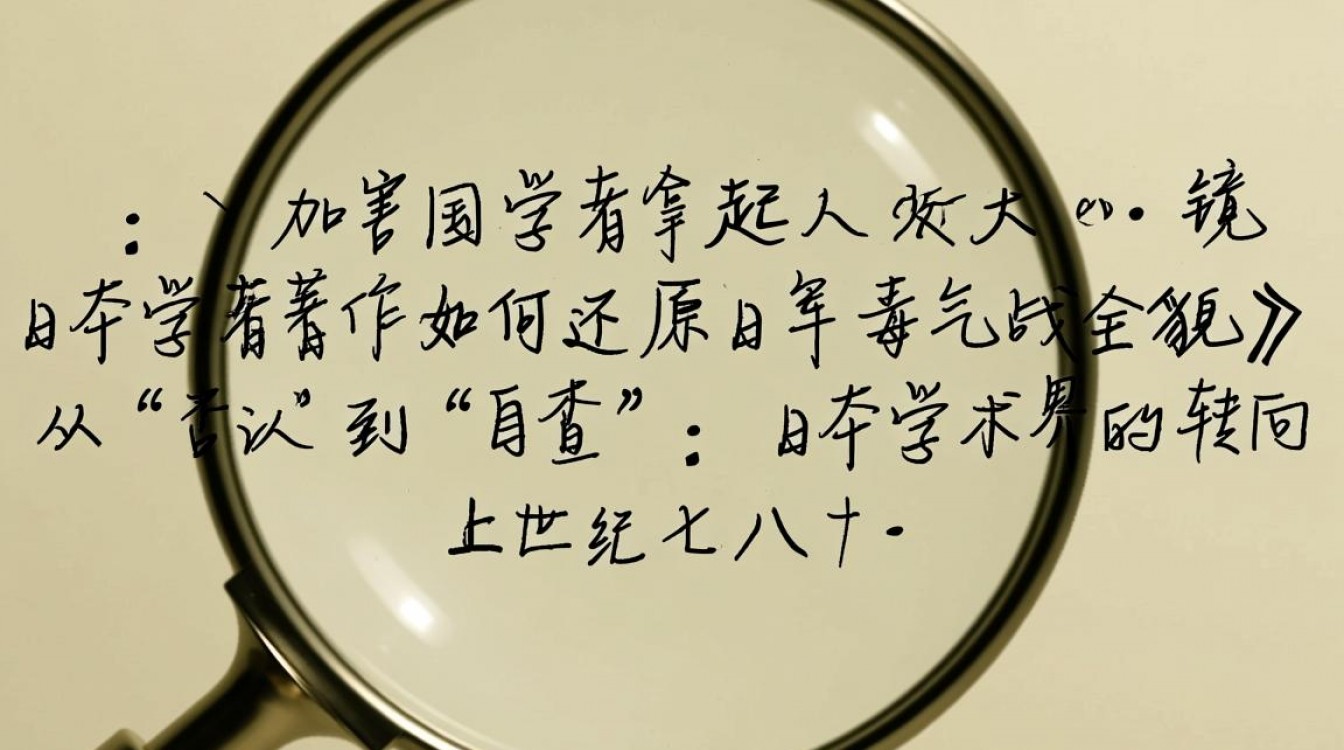
- 作战档案:吉见义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美军截获电报、日军《战斗详报》《阵中日志》合计两千余份,时间跨度从1931年“雾社事件”到1945年湖南撤退,首次把毒气战从“零星使用”改写为“系统作战”。
- 部队编制:松野诚也锁定“迫击第5大队”这支机动化毒气部队,发现其1938—1940年在中国18省区留下1241份毒气弹使用记录,仅台儿庄一役就发射1431枚,种类涵盖赤弹(呕吐性)、黄弹(糜烂性)等。
- 个人证词:学者们把战犯笔供、士兵日记、军医实验记录与中方受害者口述交叉比对,证实日军曾在南京、广州、晋南等地对平民集中施毒,造成20余万人直接伤亡,并留下贻害至今的污染区。
一本“全史”的诞生——《日军的毒气战》
2015年,吉见义明将30年搜集的材料汇编成日文版《日军的毒气战》,2022年中文版问世,全书700余页,以“研发—实战—掩盖”三幕式结构,首次完整呈现:
- 1925年日本签署《日内瓦议定书》后仍秘密建立“登户研究所”,量产毒剂;
- 1937年起,参谋本部下达“大陆指第452号”等密令,把毒气弹列为“决胜兵器”;
- 战败前后,陆军省下令“能焚毁的焚毁,能掩埋的掩埋”,并统一口径称“仅用于烟雾”。
跨国“史料外交”:把档案送到受害地
松野诚也过去五年先后向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、义乌档案馆、南京师范大学捐赠《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》《陆军登户研究所相关资料》等125份、1500余张档案影本,他说:“史料只有回到受害地,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。”这些日方原始记录,已被中国学者用于补充《中国化学武器受害地图》,为战后遗弃毒弹的受害诉讼提供关键证据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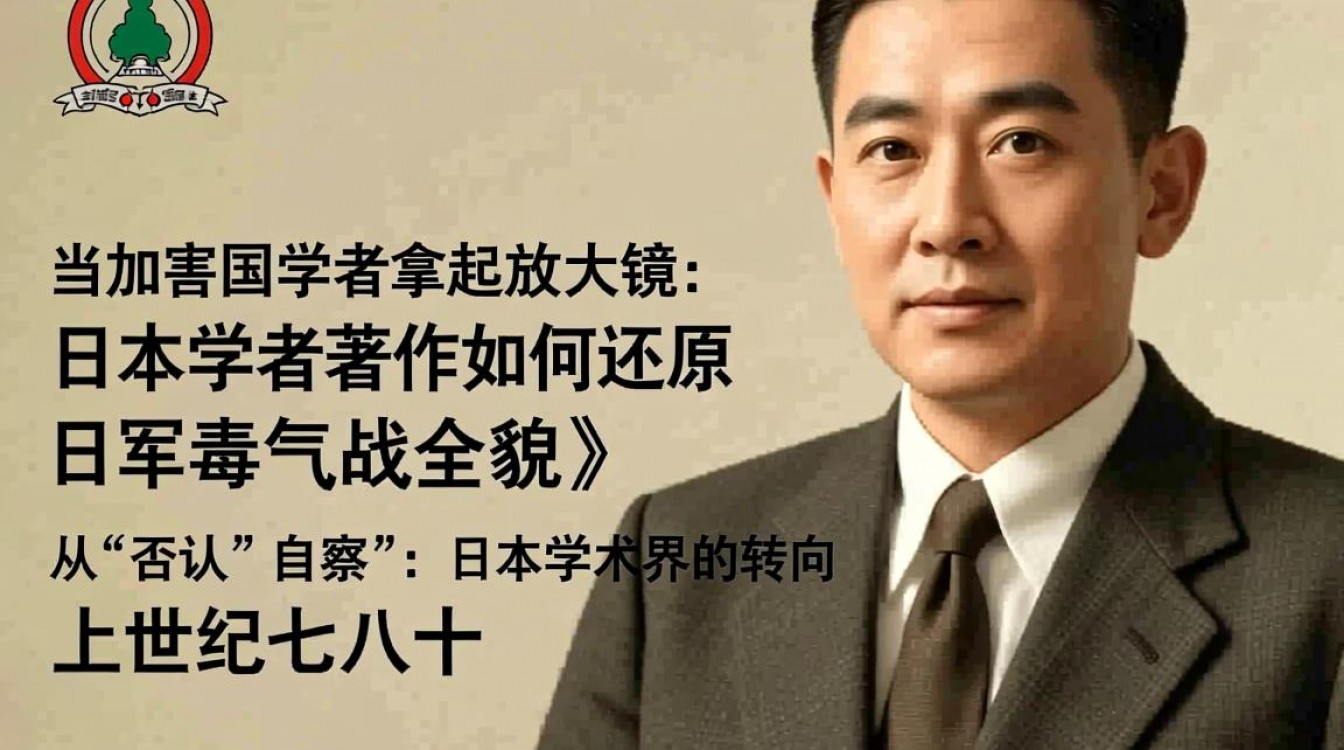
右翼压力下的学术坚守
出版日军战争罪行书籍在日本成本高昂、风险巨大,吉见义明曾接到匿名电话“别再卖国”,松野诚也的讲座也常被右翼宣传车围堵,但松野仍坚持:“历史学者的作用是查明真相,不是制造神话。”不二出版社社长小林淳子透露,类似《毒气战相关资料》这类书首印仅800册,却“每卖出一本,就为法庭、博物馆、教科书提供一枚证据”。
尚未终结的“第二战场”
学者们指出,目前公开的毒气战档案仍是“冰山一角”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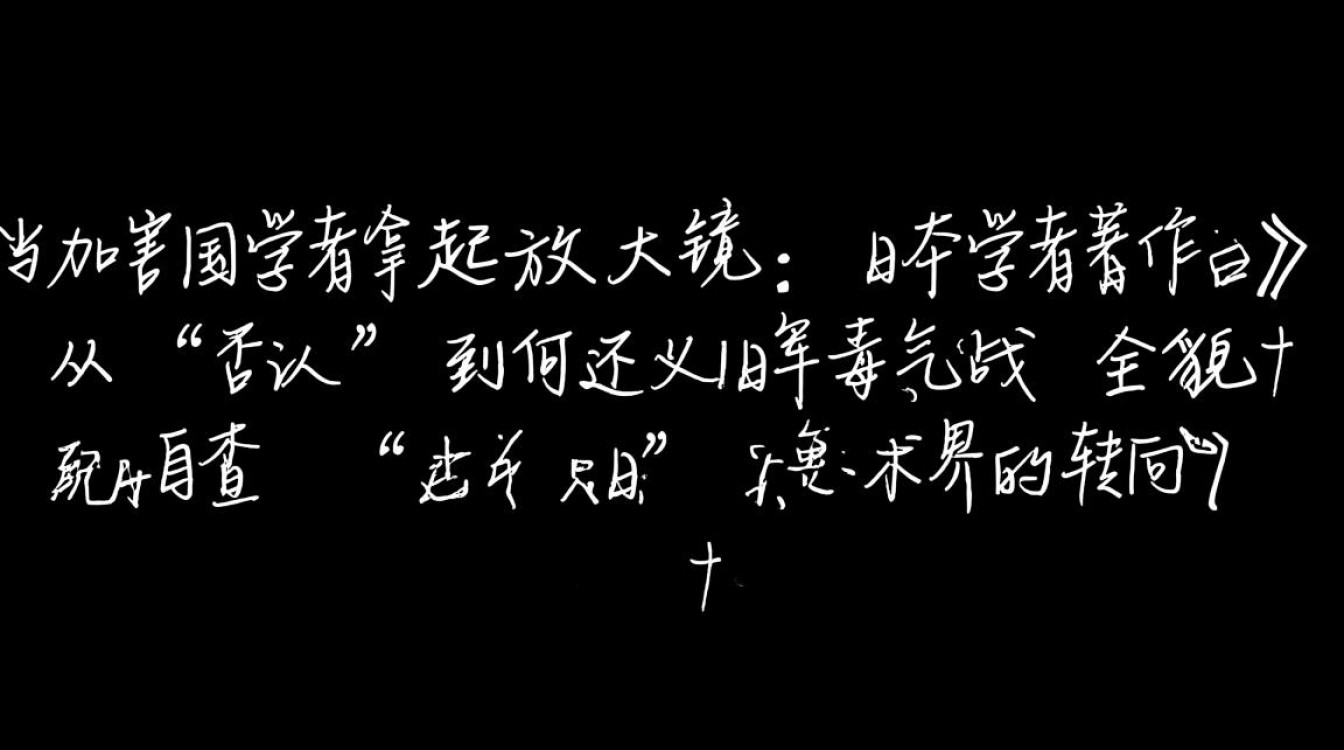
- 陆军习志野学校、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等机构的毒剂实验报告仍被封存;
- 战后美国为获取数据,与日本达成“免责交易”,部分资料留在马里兰国家档案馆,尚未完全解密;
- 日本国内仍有政客把毒气战描述为“战术烟幕”,使公众认知分裂。
吉见义明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:“只要史料还在沉睡,历史就有被篡改的可能;只要学者还在追问,真相就有被看见的一天。”
结语
当加害国学者主动拿起放大镜,历史不再只是受害者的孤证,日本学者用档案、数字与地图拼出的毒气战全貌,不仅为中国受害者提供了迟来的“日方证词”,也为日本社会设置了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:唯有在真相面前彻底低头,才能在未来真正抬头。